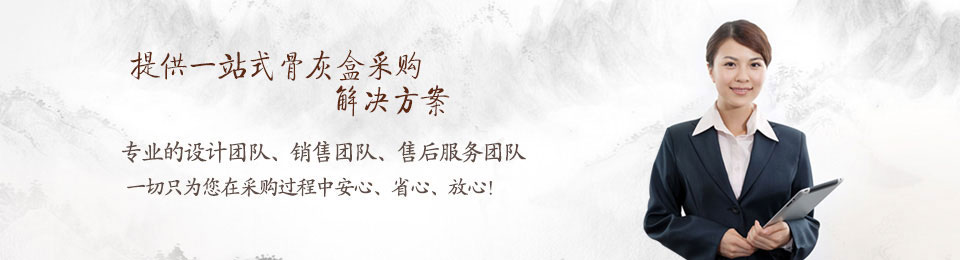搜索分类:
殡葬师:他们给了逝者最后的尊严
|
|
仔细登记每一具遗体的信息是必不可少的环节
|
|
两位工作人员正在安放逝者遗体
又到一年清明时,当人们手捧鲜花祭奠逝去的亲人时,是否记得那些曾陪伴逝者走过生命最后一程的人?
孖龙山下的清远市殡仪馆,这里每天都上演着生者与逝者的离别故事。作为一场场生离死别的见证者,他们工作最大的意义在于给予逝者最后的尊严。他们共同的名字叫殡葬师,时间让他们对生死的恐惧变得坦然,社会对他们这个行业的接纳程度也越来越高,但依然挥不去外人甚至是亲戚朋友对他们的偏见。
与老一辈的工作人员相比,年青一代的他们更多是自愿选择入行,殡葬师日趋年轻化,甚至有90后的主动投身这个特殊的行业。清明前夕,南方日报记者走近两位80后、90后殡葬师,听听他们的故事。
采写:南方日报记者 戚莹莹 摄影:南方日报记者 王良珏
80后殡葬师阿峰:时间会带走所有恐惧
每天早上8时,阿峰到达殡仪馆,换上工作服,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检查存放遗体的“冰箱”,这是他每天例行的第一道工作。在确保冷藏设备正常之后,他开始查看一天的工作安排,然后便开始给遗体清洗、穿衣、化妆、送往火化,这样的日子,周而复始。
3年前,阿峰还在深圳带着自己的团队做维修工作。偶然的情况下,被请到清远市殡仪馆维修电器。当时殡仪馆的领导看他人比较大胆,就问他愿不愿意到这边工作。“毕竟我家在清远,能回来一家人在一起也挺好的。”一家团聚固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望,但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个工作,从事了这个行业以后,他将得到什么,家人能不能接受,这些问题困扰了他两个多月。
阿峰说,当时每天都在想这些问题,幸运的是,家人觉得他要胆子够大就接受吧。“奶奶去世的时候,我一个大男人哭着从深圳回来,我明白失去亲人的感受,更希望逝者都可以得到礼遇。”85后的阿峰抽着烟,跟记者讲述着他与这个行业的故事。与老一辈殡葬师不同,他选择这个行业是出于自愿的。
三年前一个平常的上午,对于阿峰来说,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—他第一次跟着老员工接待前来认领遗体的家属。在那道安装严密的网窗后,家属看到亲人躺在那里就开始崩溃大哭了。首次遇到这种情况的阿峰,心情也不由得难过了起来。
“当时我很努力控制住自己不要表现出情绪,但我曾经失去过亲人,我太理解那种心情了。”同行的老员工看出了他微妙的情绪变化,跟他说,习惯就好了。
清远市殡仪馆坐落在孖龙山下,旁边就是孖龙山墓园。殡葬师们都要轮值夜班,晚上11∶00以后就要到场内巡视一圈,确保一切正常。回忆起第一次值班,阿峰说,晚上这里异常安静,连脚步声都可以听到,加上晚上山上的鸟叫虫鸣,首次值夜班真有背后一凉的感觉。“我告诉自己咬咬牙就过去了,无论有什么都要完成工作,不能半途而废。”这样的夜晚经历了一次、两次、三次……如今,谈起值夜班,阿峰一笑而过。
时间带给他最大的改变,“一切习惯就好。”这是阿峰说得最多的话。
90后女殡葬师林静:胆大心细更符合行业要求
第一眼看到林静的时候,要不是那一身深蓝色的工作服,实在难以将这个戴着黑框眼镜,剪着利索短发,一脸朝气的90后女生与殡葬工作联系起来。
与阿峰不同,林静是科班出身。当年林静高考结束准备填报志愿时,她在志愿填报参考书上看到了“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”,她觉得很好奇,虽然这个专业在外人看来很特殊,但她却坚持选择了这个专业。“其实当时看到这个专业名称的时候,心里是发怵的。但经历过亲人离世那种手足无措的感觉,我还是觉得应该选这个专业。”林静后来到长沙民政学院上学,就读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。
父母对林静的选择还是理解与支持的,唯一担心的事情就是以后不好找对象。但林静却没有太担心,她笑着说:“能理解是最好的,不能理解的话一个人过也挺潇洒的。”
一年半前,林静应聘到了清远市殡仪馆,主要负责遗体化妆。相对于她之前负责遗体整容的工作,遗体化妆似乎听起来好一点。
谈起第一次接触遗体化妆,林静还记忆犹新。“那是一位从18楼坠楼而亡的老人,脑里面基本上是空的,肚子也受压破开了,大腿两侧都有伤……”那时的林静还在西安的一家殡仪馆实习,那是她与同学第一次参与遗体整容化妆。还没进去,他们就被实习老师拦住,老师严肃地告诉他们,由于遗体伤势严重,需要对遗体做很大的修复,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最后,林静负责缝合遗体的腹部,配合老师做头部的修复。大胆的她,在下针的那一刻手都没有抖一下。
林静说,他们专业连续三届招收的女同学都比男同学要多。因为女生的“胆大心细”更符合殡葬行业的需求。
(本文所有人字名字均为化名)
记者手记
从不主动参加宴会
从不说再见
对于殡仪馆的一线员工来说,时间可以让他们走出负面情感,走出恐惧,但却始终逃不过来自外界的偏见。
从业3年,阿峰身边很少亲戚知道他的工作,而他的朋友圈在知道他的工作以后也迅速缩小。“如果以前我可以一次约20个朋友出来玩,现在还能一起玩的只剩下4个了……”从从业开始,他就很少跟亲戚朋友见面。他说,亲戚朋友有喜事也不怎么叫他,甚至有些提起他的职业会说他是一个“搞尸体”的。殡仪馆的副馆长告诉记者,他们早就有共识了,别人的宴会一般不积极主动参加,别人不邀请也理解。
阿峰不久前当了爸爸,职业让他不由得考虑工作对孩子成长的影响。“我一直觉得我从事这个行业问心无愧,是在为逝者服务。小孩子以后受到歧视,我会努力安慰他,争取他的理解。”和大多数同事一样,他想到的是以后在孩子的各种档案资料上,父亲的职业他只会填“民政局员工”。
相对来说,80、90后或许对这个职业的接纳程度更高。林静告诉记者,她的亲戚同学都知道她的职业,放长假回家,还会主动邀请她去做客。脱下那一身工作服,林静还是那个活泼,爱逛街、爱骑自行车的女孩。与香港作家西西笔下的《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》大相径庭。
“虽然我们在工作中比较严肃,但我们都很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,为的就是让家属悲痛的心情好受一些。”阿峰说,“每个人都会有死亡的一天,换位思考,我们也不希望将来亲人甚至是自己来到这里被粗暴对待。”对于这点,班长老刘也深有同感。
在采访结束时,沉默的老刘问记者是不是他们的样子会见报,他说担心一旦亲戚朋友在报纸上见到他们,就更不愿意来往了。道别时,副馆长摇摇头说,他们不跟别人说“再见”,这是他们不约而同的特殊习惯。(编辑:沈阳灵益www.4444448.com)
下一篇:日本独特的生前葬上一篇: 英国女子烟花葬骨灰被制成烟花
相关资讯
公司新闻推荐
同类文章排行
最新资讯文章
您的浏览历史